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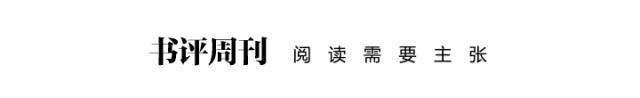 泸深投
泸深投
上帝在人间造了一所大学,委派天使来考察。天使落定象牙塔,为眼前一幕所震惊:眼下这所大学乌泱泱地乱成了一片,有胡说八道的,有投机取巧的,有强取豪夺的,就是没有追求真理的。天使疑惑不解,招来两位学者问询。
第一人说:没有设立严格的惩罚制度,人一旦缺了约束,就会作恶。天使说:有啊,学校不是制定了各种反腐败机制和举报制度吗?第二个说:没有设立好的激励制度,学校不奖励追求真理的人,多数人搭便车。天使说:有啊,学校不是设立了各种学术基金以及名誉头衔吗?大棒不顶用,还是胡萝卜不够用?三者争了起来。
正当天使悬而未决时,第三个人从塔下经过,悠悠地说道:跟制度无关,主要还是人不行。天使低头一看,眼见一优雅的白发人士,叫道:怎么不行啦,他们不都是社会的拔尖者吗?白发人不屑地说:多是些占了位子的骗子、混子和流氓。
天使从塔尖飞到塔底,义正词严地说:那也是百里挑一者呀。白发人答:扩招进来的。天使疑惑地问:扩招怎么就不行了。白发人摸了下眼镜:他们从不了解大学的初心,只把大学当作上升的通道,发论文当作谋生的工具。
天使说:那怎么才能改变他们呢?白发人又答:你在想什么呢?骗子会绕开惩罚,流氓会滥用激励,混子躺平啥都不理,早日放弃幻想。天使着急地问:那总不能置之不理吧?白发人平静地说:统统赶走,把追求真理的事业还给真理的门徒。
第一人是法学家,第二人是经济学家,第三人就是著名的英美哲学家麦金太尔。麦金太尔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习惯在别人信心满满的时候泼凉水的人。他不相信胡萝卜,也不相信大棒,其期望较低,只相信仅小的一部分人,是一位坚守自身理念的异类。
当地时间5月21日,哲学家、伦理学家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Chalmers MacIntyre)逝世,享年96岁。这段由本文作者虚构的对话正是为展现其对于社会的敏锐洞察力。作者认为,相较于作品本身的学术价值,麦金太尔的文本中蕴含的社会意义更为重要:他作为一种面对堕落的负反馈力量向我们挑明了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
下文期望以反思麦金太尔作品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当代重要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为方便读者阅读,在反思他的思想以前,将从人类价值活动的特征出发,先简单介绍他的工作性质以及他的目标,而后再借《德性之后》说明其工作思路。
 撰文 | 陶力行
撰文 | 陶力行 人类价值规范与麦金太尔的哲学活动
人类价值规范与麦金太尔的哲学活动麦金太尔的工作一般被划定在规范伦理学范畴。所谓规范,用比喻的说法,即人类评估自身及其行为时所依赖的价值量表(metrics)。量表是一种内嵌于人类认知系统的意识结构,即便没有哲学家用语言挑明其存在,它也会左右人的行为,因为人的实践无法摆脱自身条件的影响。基于分类学的正交性与完备性原则,我们可以将价值量表分为三类,即“多少表”、“正负表”以及“高低表”。多少表根据数量的多寡定好坏,正负表根据标准线的满足与否定好坏,高低表根据特定语境下的超越性程度定好坏。
例如,一将领为救一村人的性命采纳了一种激进战术,结果导致十名下属士兵阵亡。多少表下,该行为会被认为是好的,因为十人少于一村人。又例如,在一个规定不准说假话的共同体内,一个人为保护别人说了假话。正负表下,该行为是错的,因为不说假话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金律。还例如,侵略者到来,国家需要人保卫家园,但所有人都知道率先挺身而出者必先成炮灰。高低表下,最先站出来的人会被认为是好的,因为他超越了别人。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1929-2025),当代西方著名伦理学家,也是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中社群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著作包括《追寻美德》《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等。
自休谟以来,当代学者将伦理学分成元伦理学和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用“是”发问,讨论“什么是价值规范”,规范伦理学用“应该”发问,讨论“我们应该推广什么样的价值规范”。两者差别可理解为,前者在描述量表,后者在推广量表。但日常语境下的研究者经常无法在行为上分离两者。一个人留意何种量表,就会以为何种量表重要,继而顺势推广这张量表。例如,若一研究者认为最重要的元问题是明晰行为边界,那他就会在力推正负表;若一人相信最重要的元问题是测量行为后果,那他就会力推多少表。
依笔者见,伦理学家无非就是些拿着价值量表修补话语的人,他们通过生产新概念和叙事以令既定话语更显系统和连贯。例如,申不害、慎到根据多少表原则,分别引入“术”与“势”等概念以修补法家话语。但是,绝对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不可能实现,因为任何有生命力的话语都是开放的,其会随人类经验的累积而迭代。因此,话语分析时,常会发现有些话语的叙事受多种量表支配的情况。例如,儒士们一会儿手抓高低表,谈礼义仁智信,一会儿手握多少表,论士农工商四大支柱。
伦理学家的修补不是毫无目的的,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将某一量表提升至霸权地位。庄子讲无私乃天道,竺可桢讲“只问是非,不计利害”都可理解为将高低表拱上霸权地位的表现;不少家长教育自家子女时常说的“要先改变社会,就要先适应社会”“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则是将多少表置于霸权地位的表现。人的动机是多样的,任何一张量表都存在合理性,所以任何量表都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成为主导决策的霸权性条件。
由于多数哲学家脑子比较简单,不接受复杂性,总会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对于简单、纯粹的偏好强化成看世界的滤镜,误以为只有一种表的存在才合理,于是片面追求各种“主义”,竭力将某张表的地位做大做强。支持多少表的功利主义、支持正负表的义务论主义以及支持高低表的德性主义,正是当代规范伦理学演化出的三种片面主义。有学者尝试建立大一统理论,要么通过重组概念以用一种表通约另两张表,要么通过建立更精密的论证以取消两张表的合法性。然而,两种做法均不会成功,因为三张表的分类已满足正交性和完备性原则,进一寸退一寸都不影响大局。
麦金太尔是德性派主将。根据其在《德性之后》(也有译作《追寻美德》)的自述,可将其工作概括为以下两点(参见《德性之后》第二章末尾):一、提升高低表的地位;二、引入实践(practice)概念以包装高低表。第一项工作算是立场之争,表明他与亚里士多德等人结成了思想联盟。第二项工作算修补工作,表明他能灵活调用当下流行的思想工具箱以修补德性话语。规范伦理学脉络下,麦氏工作属于累积式创新,在德性伦理学脉络下,算是破坏式创新。接下来,笔者将以麦金太尔的《德性之后》为例,说明其工作方式。
麦金太尔。
简单概述《德性之后》的写作策略:第一步,寻找现代多少表和正负表支持者的立论基础,即人性中的情感条件,通过指出情感论本身的问题以削弱多少表和正负表的正当性;第二步,回溯并归纳历史上支持高低表的理论,指出古典高低表的立论基础是特定的社会条件;第三步,挑出高低表支持者中最易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亚里士多德理论,指出亚氏理论虽假定的目的论作为逻辑起点有问题,但结论是对的;第四步,引入新概念“实践”,通过调整逻辑起点修复亚氏理论。
要理解麦氏的工作,我们需要将其置于三百年的时间尺度下审视。十八世纪起,西方进入基督教话语退场的大转型时代。西人在当时认为此过程是积极进步的,遂用“启蒙”这一漂亮语词为其冠名。十八世纪前的西方世界,规范话语主要由基督教提供,但十八世纪起,当西人的日常经验随资本主义的胜利得到极大扩展后,传统的基督教话语进入衰退期。当控制规范的话语空间出现意识形态裂缝后,持多少表和正负表的启蒙哲人率先从角落里冒了出来,有休谟、康德,还有密尔、边沁。他们是替代性话语的缔造者。至于麦金太尔,则是手执高低表的后来居上者。
基督教话语在十八世纪是一种建制性话语,当该话语逐步退场却又没有其他建制性话语——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话语——顶上时,非建制或尚未建制化的个体主义/自由主义话语迅速跟进,出现了康德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的社会景观。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启蒙哲人作为个体性话语的发声筒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普遍思考以下问题:基督教不定规范了,那么规范由谁来定?如果人人都觉得规范不重要,社会乱了怎么办?对启蒙哲人而言,建立新的霸权性规范很必要,否则人类社会将陷入无止境的冲突之中。
《追寻美德》(第三版)
作者: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
译者: 宋继杰
译林出版社2024年5月
构建新时代的规范不仅需要契合新的生活经验,还要在本体论层面充分肯定个体。按照启蒙哲人的说法,基督教话语的退场换来的是人性的解放。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转向人性思考,并宣称未来的规范理应顺应人性。情感,是启蒙哲人从人性框架中锚定的基石。休谟就曾宣称,人们对于行为的价值判断并非通过推理获得,而是源自个人的情感偏好。边沁也类似地指出,善是能够增进幸福和快乐的行为。这里的不喜欢、幸福与快乐,都属人的情感体验。
麦金太尔将启蒙哲人尝试从人性中的情感要素推导出普世量表的做法统称为启蒙的筹划(The Enlightenment Project)。从情感角度思考价值规范很符合当代人的日常直觉。但康德认为,诉诸情感会抽空规范,因为情感多变,而规范不应该多变。于是,他引入道德律概念以修补情感理论,指出:人们的价值判断契合某种不以个人意志为导向的法则。对康德而言,法则虽看不到,但如同牛顿力学一般刚性存在,需要使用将心比心法才能将其显现。
将心比心法是一种思想实验,凭此可以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范。康德引入该法,旨在给人留下“自主选择”的空间,因为即便法则不是个人制定的,但对于法则的把握依旧隶属于个人。问题是,将心比心也依赖于感受。麦金太尔对康德方案表示怀疑:假定某个人觉得见利杀人是对的,且将心比心地觉得别人见利杀人也是对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按照情感原则,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杀人?麦氏认为,指望从情感推导出普世的价值规范是一种妄念。
麦氏劝人们放低预期,甭指望通过推广一种自上而下的规范来消解分歧与冲突,因为分歧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麦氏看来,无论天使举大棒,还是抛胡萝卜,都不能解决大学的乌泱泱问题,除非引入新鲜血液。麦金太尔的目的是提升高低表。其挑出诸多涉及美德的经典文本作分析,指出:虽然不同的古典文本会有迥异的说法,但他们在谈及美德时,都会考虑具体的社会语境。例如,当一个人扮演士兵角色时,他会被期望表现得勇敢,当一个人扮演工匠角色时,他就会被期望表现得有耐心。
麦氏的意思是:在古典文本中,规范的正当性来源于行动者在特定语境下扮演的社会角色,因为一种角色对应一种规范,只要个体进入角色,他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因角色扮演而必须服从的规范。但是,麦金太尔对古典文本表示疑虑:若对美德的规范性要求源自社会角色,那追寻美德似乎是不是就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义务行为了?难道行动者会甘愿服从岗位的要求吗?麦金太尔是决然不会相信:当了教授的人就一定会好好当教授的。
《依赖性的理性动物》
作者: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
译者: 刘玮
译林出版社2013年10月
相比于其他高低表支持者,麦氏更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因为亚氏保留了个人的自主性。亚氏指出,人有一种追求内在善的目的,而践行美德是一种实现内在善的手段,为实现内在善,人必将践行美德。但麦氏并不接受该说法,不仅因为追求内在善是一种形而上假定,还因亚里士多德高估了人性。麦金太尔的策略是引入“实践”概念以代替目的论概念。所谓实践,是指人类在社会过程中分化出来的有特定目标指向的协作性行为,包括唱歌、跳舞、建筑、烹饪等。麦氏认为,个体一旦实践,就会力图实现卓越。
所谓美德,就是个体为实现其眼中的卓越而为自己设置的规范。一个练习生刚开始学钢琴时,就想熟练地弹奏完一支曲。他重复练习,第一星期要中断十五次才能完成,第二星期只需中断八次,至第三星期,中断已减至三次。当一支曲子练熟了,就会转向另一支曲子的练习。麦氏认为,正是因为练习生切身投入实践,他才会自然而然地保持耐性——这是他为了实现卓越而必须遵循的规范。
总结一下麦金太尔的思想:
一个人会占据某岗位,但并不会因此就下场实践,如那些在岗位上摸鱼的人。只有那些心怀实践意愿的人才会实践。一个人一旦参与实践,他就势必会自设目标与规范,并付之于相匹配的持续行动。因此,天使与其想着层层加码式地改革大学,不如让该离开的离开,留下那些有着超越意识、拿着高低表行事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实践追求真理的事业,只有他们才知道如何搞好一所大学。
三张表是人类心智的意识结构,先于人的思维活动而存在,所以花时间去寻找三张表的存在依据纯属浪费时间,无论把情感还是实践当作原点,都可以,也都无所谓。麦金太尔花大量笔墨批判近代哲学家把情感当作量表的逻辑起点或引入实践概念修复量表,不影响任何量表的合法性,毕竟一个立场能否得到支持不取决于该立场本身是否可靠——只取决于是否有人信。如同麦氏本人一样,即便不认同亚氏的逻辑起点,也依然可以丝滑地接受亚氏理论的终点。
量表的表达高度依赖于环境。量表是否有机会表达,取决于是否有权力加持,而非用以表达的话语是否连贯。话语连贯是哲学家关心的事,不是话语使用者关心的事。前现代时期的大多数文化圈内,多少表的表达都受到抑制,那是因为各社会的整体增长有限,多少表的表达缺乏正向反馈。可当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给予多少表的表达以正向反馈后,连自古以来对多少表都持否定态度的宗教权力也会发生态度上的转变。如新教人士随资本主义扩张而改革话语,鼓励努力工作、创业。
麦金太尔。
麦氏搞错的是,他以为正负表和多少表的崛起是启蒙的筹划。其实不是。它们的崛起只是时代变迁的内生性产物而已,本身是结果而不是原因。高低表盛行于以精微调适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空间里,因为在流动性慢、眼光比较局限、个人生活策略仍以路径依赖为主的空间里,个体只会专注手上事业。但流动性变强之后,个体的注意力开始转移,手上事业开始变得不再重要,分配的问题、算计的问题就会冒出来。对于多数人而言,如何以手上事业的名义搞钱、权、名变得重要。
大学里评审教授,原来以求是创新为主要话语,评审依据主要是知识的生产能力。可当各种歪瓜裂枣挖空心思地进入大学后,靠关系的、靠权力的、靠钞票的场外力量就变得重要。求是创新者的自我繁殖抵不上歪瓜裂枣者的繁殖,当前者出现明显的人口劣势时,高低表自然会受到抑制。歪瓜裂枣者不是不知道目前大学的问题,但是他们会用层层加码的正负表和多少表手段扭曲原本的求是创新体系。在此情况下,改革越多,问题越严重。麦金太尔看清了这一点。
麦金太尔觉得引入实践概念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其指出一个人一旦下场实践,就会自设规范与目标。问题在于,不同人会因对实践的理解不一样,设置出不一样的规范和努力方向。有些人把大学理解为不错的阶级跃升通道,于是把进大学搞钱当实践,有些人把大学当作不错的生态位,于是把进大学摸鱼当实践。当对大学有不同期待的人进入同一所大学后,大学的初心依旧会被搁置。只要歪瓜裂枣仍旧占有比例上的优势,就甭指望解决问题。重要的,不是规范,不是论证,而在于踢掉忘记初心者的力量。
这么说,并不是说麦金太尔的工作毫无意义。麦氏工作的社会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因为他向我们挑明了问题。麦金太尔看到的是狂欢下的堕落、傲慢与自以为是。他反对的,与其说是多少表和正负表,不如说是令这两张表得以不断表达的“堕落现实”。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将他以及他作品的出现视为对于现实堕落的负反馈表达。最后说一句:无论哲学家怎么说,都会有逻辑上的漏洞,所以对大多数读者而言,与其关注他怎么说,不如关注他说什么,他的动机给予我们暗示会更多。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陶力行;编辑:李永博;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泸深投
卓信宝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